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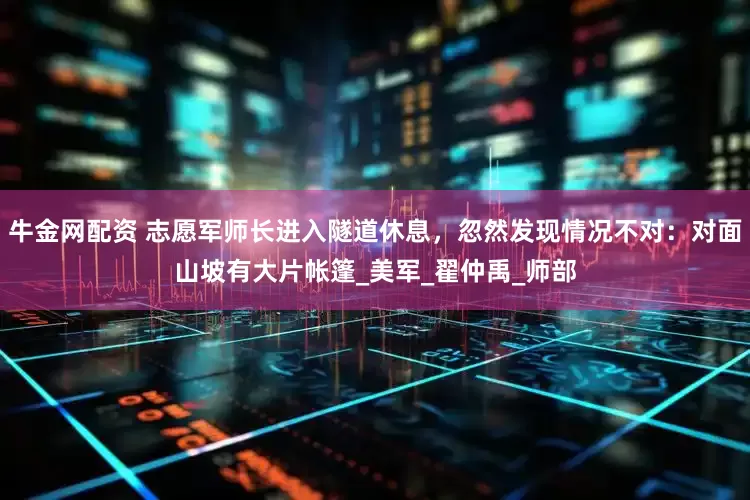
1950 年 11 月的朝鲜半岛,寒雾像浸透了柴油的破布,贴在志愿军第 114 师战士们的棉衣上。师长翟仲禹攥着冻成冰坨的望远镜,看着隧道口飘起的雪沫子,突然按住了正要生火取暖的通信兵 —— 对面山坡上,几十顶橄榄绿帐篷正冒着淡白色的炊烟,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格外刺眼。
这场意外的对峙,发生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最胶着的时刻。当彭老总 “诱敌深入” 的战略在西线全面铺开时,38 军 114 师在穿插中与主力失去联系。翟仲禹带着师部和零散部队边打边撤,钻隧道本是为了躲避美军空袭,却一头撞进了敌人的眼皮底下。
废弃隧道里的生死对峙
隧道深处还残留着火车头的煤烟味,翟仲禹用刺刀挑起一张揉皱的美军罐头标签,指尖在 “C 级战斗口粮” 的字样上划过。“这里不是友军休整过,” 他压低声音对身旁的 38 军副军长江拥辉说,“看帐篷间距,是美军的标准宿营配置,至少一个营。”
话音未落,隧道口突然闪过三道手电光。三名美军侦察兵正举着卡宾枪探头探脑,领头的士兵已经看到了隧道深处志愿军的帽檐。翟仲禹一把将身边的参谋拽进暗处,抬手就是一枪 —— 枪响的瞬间,山坡上的帐篷像被捅破的马蜂窝,美军士兵抱着枪从帐篷里滚出来,重机枪立刻在隧道口织起火网。
展开剩余64%“江副军长,您先撤!” 警卫员试图架起江拥辉,却被他甩开手臂。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正盯着隧道壁上的铁轨凹槽:“让工兵炸断铁轨当掩体,通信班跟我来,必须架起电话线!” 在纷飞的流弹中,战士们用身体护住临时架设的电话线,铜丝在冻土上拉出火花,像一条救命的血管延伸向远方。
跨越火线的救援接力
342 团政委王丕礼接到师部求救信号时,他们正卡在美军的两道封锁线之间。团部作战室里,地图上代表 114 师的红点被密密麻麻的蓝圈包围。“抽一个营,用刺刀劈开血路!” 团长的拳头砸在桌面上,搪瓷缸子震得跳起。
这个营刚冲出封锁线就遭遇了美军空袭。炸弹在雪地里炸出一个个白色的烟柱,营长看着倒在血泊里的通信兵,咬着牙下令:“分散成三人战斗组,扔掉背包,只带弹药!” 他们在弹坑间蛇形前进,冻伤的脚掌踩进融雪的泥泞,留下串串带血的脚印。
而真正改写战局的,是另一支神兵天降的队伍。113 师 337 团 3 营本在追击溃逃的美军,赵吉祥营长听到隧道方向的枪声时,正趴在雪地里啃冻土豆。“是咱们的三八式!” 他猛地抬起头,望远镜里美军帐篷的位置让他心头一紧,“全营注意,向左翼迂回,抄他们后路!”
腹背受敌的绝地反击
当 3 营的机枪突然在美军营地后方响起时,翟仲禹正指挥战士们用铁轨当盾牌。他看见美军像被驱赶的羊群般乱作一团,立刻抓起冲锋枪:“江副军长,机会来了!” 两个指挥员在硝烟中交换眼神,师部残存的兵力从隧道里如潮水般涌出,与 3 营形成夹击之势。
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。志愿军战士踩着美军的罐头盒冲锋,美军的火焰喷射器把隧道口的积雪烤得冒白烟。翟仲禹的棉衣被流弹撕开一道口子,棉絮混着血珠粘在身上,他却死死盯着被夺回的火车站 —— 那里停放着三列满载弹药的军列,正是美军突围的关键补给。
“炸掉铁轨,守住车站!” 江拥辉的吼声盖过了爆炸声。当最后一节车厢在火光中腾空而起时,天边泛起鱼肚白。赶来支援的 342 团士兵们趴在雪地上,看着师部首长与友邻部队紧紧握手,才发现自己的睫毛早已冻成冰棱。
这场隧道遭遇战,最终以志愿军收复火车站、俘虏 23 名美军告终。翟仲禹在战后总结里写道:“当敌人以为我们是惊弓之鸟时,他们忘了,志愿军的字典里没有‘绝境’。”1955 年授衔时,已是少将的江拥辉看着军功簿上 “二次战役隧道阻击战” 的记录,总会想起那个雪夜 —— 隧道口的枪声,恰是吹响总攻的号角。
正是无数这样的瞬间,让 “诱敌深入” 的战略蓝图在朝鲜半岛的崇山峻岭间落地生根。当美军最终溃退至 “三八线” 时,他们或许永远不懂:那些钻进隧道躲避空袭的中国军人,为何转眼就能变成堵住退路的钢铁闸门。这背后,是指挥员的临危不乱,是士兵的向死而生,更是一个民族在绝境中迸发的磅礴力量。
发布于:河北省网眼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